底層放棄教育,中產過度焦慮,上層不玩中國高考
作者:余秀蘭,來源:半城(ID:banchengdushu),經授權發布
越來越多的社會底層家庭的孩子放棄高中、大學,直接選擇技工學校,學門手藝和技術;5% 的上層家庭根本不玩中國高考游戲,也看不上國內質量越來越差的本科教育,這些家庭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選擇每年學費高達數十萬的國際學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歐美發達國家繼續接受最優質的教育,他們將是未來中國社會甚至國際化的精英。
對教育最抓狂和焦慮的當屬城市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的孩子輸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 大學,他們的社會流動軌跡就將滑向底層。這就是中國社會當下,生動的階層教育畫像。
《余秀蘭教授永慕廬講演》
曾經,“讀書改變命運”“知識就是力量”是社會上流行的口號。教育是中國億萬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子弟的一劑強心針。
如今,“一畢業就失業””“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等口號卻戲謔地調侃了教育,這個曾是渴望向上流動的人們賴以改變命運的獨木橋。許多令人困惑的情況出現了——
第一,“教育改變命運”的口號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已然變味。
整個社會教育的起點已經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過是最基礎與必需的教育。
受教育已不是提高個人檔次的問題,而是維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問題。
第二,教育不再是讓一個家庭脫貧致富的好事。
對于許多家庭而言,大學學費無異于天文數字。
一個人考上大學,一個家族都會被拖入貧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趨高,即使大學畢業,對家庭的回報也沒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樣可以獲得高的社會地位。
許多名人并未受過高層次的教育,但有著可觀的金錢和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謂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斷涌現,使得“讀書無用論”有了生存的土壤。
種種現象似乎表明,教育促進社會成員的升遷性社會流動的功能減弱了,高層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帶來好的收入和職業地位。
“教育改變命運”的口號不再像過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國的不同階層,對待教育的態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別。
絕望的底層人民:干脆放棄高等教育
一位兩個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長說:
讀個初中就行了,讀多了也沒用的!
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認為我目光短淺,瞧不起我,現在,他們好多人反過來求著我,讓我兒子幫他們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學又怎么樣,還不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現在,機會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學。
中科院社會學博士后的調查發現,越貧窮越認同“讀書無用”:村莊貧困層認同度 62.32 % 、農村中間層 37.24 % ;年收入1萬元以下的村莊貧困層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見,認為“讀書無用論”再次泛濫的結論并不正確。中高層從未說過讀書無用,相反,他們更加瘋狂。
瘋狂的中產階級:對教育的焦慮與過度重視
且不提一線城市天價卻依舊供不應求的名校學區房,根據今年七月的一則新聞報道,一位80后上海媽媽為今年 9 月即將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列了個學期清單,暑假開銷加課外學習的開銷達到 32 萬元。
除了各種學習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營以外,總計 20 個課外興趣班。中產階級對教育的焦慮,從中國不斷高企的學區房價和愈發火熱的補習班便可一窺全貌。
而一條新的道路越來越成為新中產階級的家庭標配,那就是讀私立學校和出國讀書。
2016 年 6 月 10 日,南京某私立學校的幼升小面試中,5086 名孩子競爭 216 個名額,錄取比例破 23:1。
而其如此受歡迎的原因,與該校針對出國留學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關系。
孩子的教育問題集中反映了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
中產階級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繼續接力,向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躍遷,為此他們不惜重金,讓孩子去上各種輔導班,學習各種才藝和禮儀,讓孩子贏在起跑線;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會轉而擁抱階層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繼承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為此他們不惜擱置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會堅定地反對異地高考,將招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貶稱為“菜場小學”,避之不及。
中產階級的孩子,也許是學業壓力最大的一個群體,這源于他們父母內心深處巨大的不安全感:畢竟,與社會上層相比,他們的孩子輸不起。
這些現象都帶給人們極大的困惑:教育還能改變命運嗎?底層的上升通道關閉了嗎?教育與社會流動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人們為什么討厭那些“二代”?
觀察當前的中國社會可以發現,社會階層固化趨勢顯現,向上流動困難。
第一,教育面前機會不平等的現象仍很嚴重。
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中國夢宣傳教育系列報告會”八場報告中指出,我國教育公平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表現在城鄉、區域、校際、群體“四大教育差距”方面。
以上這些教育差距(除第四個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時也有家庭社會經濟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為孩子提供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差距越來越大。
具有較好社會經濟條件的家庭會為孩子選擇較好的教育。此外,家長在學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條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條件好的家庭可以為孩子找家教、選擇輔導班和進行各種才藝培訓。
這些,都導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擁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優勝劣汰公理遭“二代”現象挑戰。
“二代”現象反映了社會差別通過代際更替具備一定的遺傳性,上代的優勢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放大和強化而傳遞給下代。
在地位獲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優勢可以通過影響下代的教育水平,從而影響下代的地位獲得,即上代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使他們在教育競爭中獲得優勢,進而在地位獲得上取得優勢;
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下代獲得較好的職位。有研究表明,社會就業競爭越激烈,社會資本運作的空間就越大。
“拼爹”是對這一現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擴張,獲得大學文憑不再是件困難的事情,但大學文憑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
對于某些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好的學生來說,大學文憑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們的就業不需要完全依靠這張文憑;
而對于家庭社會背景差的學生來說,大學文憑則具有實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們找工作的唯一資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讓丹所指出的:
雖然文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認為為了獲得某一社會職位有文憑就足夠了。
現實中,擇優錄用的運作似乎被社會因素嚴重扭曲了。在學業成功和選擇某一教育與家庭環境不無關系的事實之外,社會出身繼續對教育水平相當的青年們的職業插入產生影響,并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繼續介入其中。
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了底層人們向上流動受阻,對教育絕望。
而中產階級,卻開始了地位焦慮和對教育的瘋狂。社會階層結構變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為人生贏家。
與此同時,社會矛盾極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為了諸多社會矛盾的來源,和一觸碰就燃起熊熊輿論之火的敏感詞。
寒門學子,除了努力還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進升遷性的社會流動?
事實上,這取決于大的社會結構,當一個社會是開放公正的,人們的地位獲得主要依靠其知識與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會較大;
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封閉固化,人們的地位獲得主要依靠先賦因素,依靠對上代優勢的“繼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其次,取決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是否公平地向每個階層的人開放,教育中是否不帶有任何階級偏向。
因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進合理的社會流動。此外,還要考慮教育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同經濟發展之間的匹配性。
這就是說,教育能否促進底層的升遷性社會流動,并不僅僅是由教育本身決定的,還受社會因素制約,而且歸根結底是社會結構起決定作用。
只是,寒門學子,除了努力還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棄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棄改變命運的機會?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
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說過:面對經濟資本和社會權力,文憑雖然只是“一個日漸疲軟的通貨”,但是中國中產階級孩子除了拼高考,還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隱秘再生產的途徑。
上層階級的父母用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為子女提供了最優質且稀缺的教育資源,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只和同樣社會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層精英封閉的人際網絡。
底層社會放棄高等教育這個中產階級的孵化器,將世代都是藍領個人。
而中產階級家庭多數孩子在普通大學畢業后將成為低收入的低級白領,要么是城市貧困群體,要么繼續啃老。
這是合理的現象嗎?政府的責任何在?父母該為孩子的階層負責嗎?這些,或許都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演講者:余秀蘭
來源:半城(ID:banchengdushu),已獲授權
《余秀蘭教授永慕廬講演》
時長:24:51分
越來越多的社會底層家庭的孩子放棄高中、大學,直接選擇技工學校,學門手藝和技術;5%的上層家庭根本不玩中國高考游戲,也看不上國內質量越來越差的本科教育,這些家庭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選擇每年學費高達數十萬的國際學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歐美發達國家繼續接受最優質的教育,他們將是未來中國社會甚至國際化的精英。對教育最抓狂和焦慮的當屬城市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的孩子輸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學,他們的社會流動軌跡就將滑向底層。這就是中國社會當下,生動的階層教育畫像。
曾經,“讀書改變命運”“知識就是力量”是社會上流行的口號。教育是中國億萬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子弟的一劑強心針。
如今,“一畢業就失業”“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等口號卻戲謔地調侃了教育,這個曾是渴望向上流動的人們賴以改變命運的獨木橋。許多令人困惑的情況出現了——
第一,“教育改變命運”的口號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已然變味。整個社會教育的起點已經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過是最基礎與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個人檔次的問題,而是維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問題。
第二,教育不再是讓一個家庭脫貧致富的好事。對于許多家庭而言,大學學費無異于天文數字。一個人考上大學,一個家族都會被拖入貧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趨高,即使大學畢業,對家庭的回報也沒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樣可以獲得高的社會地位。許多名人并未受過高層次的教育,但有著可觀的金錢和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謂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斷涌現,使得“讀書無用論”有了生存的土壤。
種種現象似乎表明,教育促進社會成員的升遷性社會流動的功能減弱了,高層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帶來好的收入和職業地位。“教育改變命運”的口號不再像過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國的不同階層,對待教育的態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別。
1
絕望的底層人民:干脆放棄高等教育
一位兩個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長說:“讀個初中就行了,讀多了也沒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認為我目光短淺,瞧不起我,現在,他們好多人反過來求著我,讓我兒子幫他們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學又怎么樣,還不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現在,機會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學。”
中科院社會學博士后的調查發現,越貧窮越認同“讀書無用”:村莊貧困層認同度62.32%、農村中間層37.24%;年收入1萬元以下的村莊貧困層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見,認為“讀書無用論”再次泛濫的結論并不正確。中高層從未說過讀書無用,相反,他們更加瘋狂。

△講演現場
2
瘋狂的中產階級:對教育的焦慮與過度重視
且不提一線城市天價卻依舊供不應求的名校學區房,根據今年七月的一則新聞報道,一位80后上海媽媽為今年9月即將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列了個學期清單,暑假開銷加課外學習的開銷達到32萬元。除了各種學習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營以外,總計20個課外興趣班。中產階級對教育的焦慮,從中國不斷高企的學區房價和愈發火熱的補習班便可一窺全貌。
而一條新的道路越來越成為新中產階級的家庭標配,那就是讀私立學校和出國讀書。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學校的幼升小面試中,5086名孩子競爭216個名額,錄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歡迎的原因,與該校針對出國留學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關系。
孩子的教育問題集中反映了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中產階級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繼續接力,向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躍遷,為此他們不惜重金,讓孩子去上各種輔導班,學習各種才藝和禮儀,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會轉而擁抱階層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繼承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為此他們不惜擱置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會堅定地反對異地高考,將招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貶稱為“菜場小學”,避之不及。
中產階級的孩子,也許是學業壓力最大的一個群體,這源于他們父母內心深處巨大的不安全感:畢竟,與社會上層相比,他們的孩子輸不起。(熊易寒:中國中產階級的三副面孔,《文化縱橫》2016年8月)
這些現象都帶給人們極大的困惑:教育還能改變命運嗎?底層的上升通道關閉了嗎?教育與社會流動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余秀蘭教授在講演現場
3
人們為什么討厭那些“二代”?
觀察當前的中國社會可以發現,社會階層固化趨勢顯現,向上流動困難。
第一,教育面前機會不平等的現象仍很嚴重。
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中國夢宣傳教育系列報告會”八場報告中指出,我國教育公平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表現在城鄉、區域、校際、群體“四大教育差距”方面。以上這些教育差距(除第四個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時也有家庭社會經濟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為孩子提供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差距越來越大。具有較好社會經濟條件的家庭會為孩子選擇較好的教育。此外,家長在學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條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條件好的家庭可以為孩子找家教、選擇輔導班和進行各種才藝培訓。
這些,都導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擁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優勝劣汰公理遭“二代”現象挑戰。
“二代”現象反映了社會差別通過代際更替具備一定的遺傳性,上代的優勢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放大和強化而傳遞給下代。在地位獲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優勢可以通過影響下代的教育水平,從而影響下代的地位獲得,即上代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使他們在教育競爭中獲得優勢,進而在地位獲得上取得優勢;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下代獲得較好的職位。有研究表明,社會就業競爭越激烈,社會資本運作的空間就越大。“拼爹”是對這一現象最形象的概括。


△講演現場
由于高等教育的擴張,獲得大學文憑不再是件困難的事情,但大學文憑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對于某些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好的學生來說,大學文憑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們的就業不需要完全依靠這張文憑;而對于家庭社會背景差的學生來說,大學文憑則具有實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們找工作的唯一資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讓丹所指出的:“雖然文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認為為了獲得某一社會職位有文憑就足夠了。”“現實中,擇優錄用的運作似乎被社會因素嚴重扭曲了。在學業成功和選擇某一教育與家庭環境不無關系的事實之外,社會出身繼續對教育水平相當的青年們的職業插入產生影響,并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繼續介入其中。”
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了底層人們向上流動受阻,對教育絕望。而中產階級,卻開始了地位焦慮和對教育的瘋狂。社會階層結構變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為人生贏家。與此同時,社會矛盾極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為了諸多社會矛盾的來源,和一觸碰就燃起熊熊輿論之火的敏感詞。

△講演現場
4
寒門學子,除了努力還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進升遷性的社會流動?
事實上,這取決于大的社會結構,當一個社會是開放公正的,人們的地位獲得主要依靠其知識與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會較大;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封閉固化,人們的地位獲得主要依靠先賦因素,依靠對上代優勢的“繼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其次,取決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是否公平地向每個階層的人開放,教育中是否不帶有任何階級偏向。因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進合理的社會流動。此外,還要考慮教育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同經濟發展之間的匹配性。這就是說,教育能否促進底層的升遷性社會流動,并不僅僅是由教育本身決定的,還受社會因素制約,而且歸根結底是社會結構起決定作用。

△現場讀者認真地做筆記
只是,寒門學子,除了努力還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棄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棄改變命運的機會?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
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說過:面對經濟資本和社會權力,文憑雖然只是“一個日漸疲軟的通貨”,但是中國中產階級孩子除了拼高考,還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隱秘再生產的途徑。上層階級的父母用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為子女提供了最優質且稀缺的教育資源,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只和同樣社會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層精英封閉的人際網絡。底層社會放棄高等教育這個中產階級的孵化器,將世代都是藍領個人。而中產階級家庭多數孩子在普通大學畢業后將成為低收入的低級白領,要么是城市貧困群體,要么繼續啃老。
這是合理的現象嗎?政府的責任何在?父母該為孩子的階層負責嗎?這些,或許都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永慕廬論壇半城大話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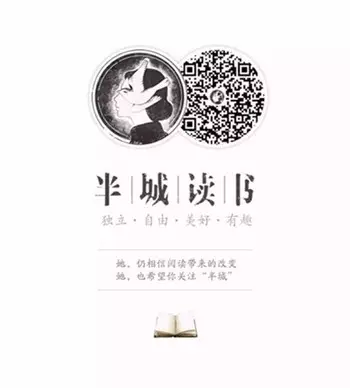

感謝閱讀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
來源:中國經濟學人

 已關閉
已關閉
 懸賞分:15 -
提問時間 2016-09-19 13:51
懸賞分:15 -
提問時間 2016-09-19 1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