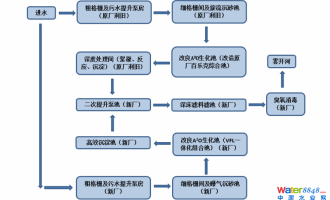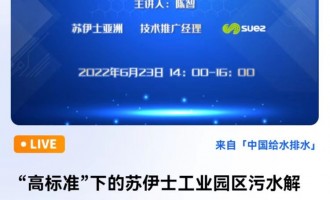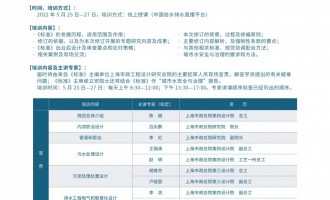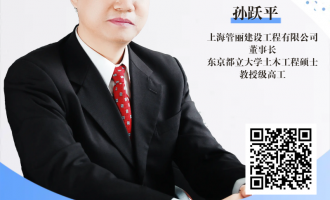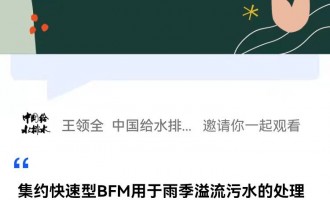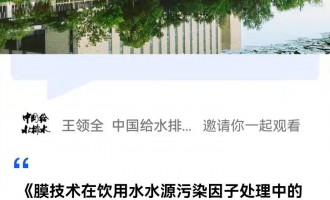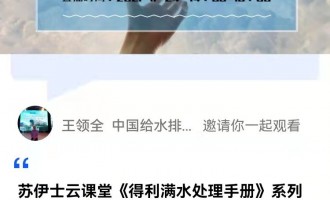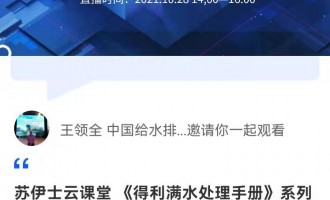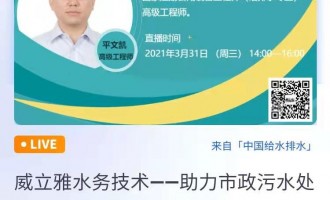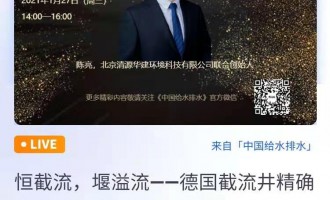斬斷危廢處理層層轉包黑產鏈
斬斷危廢處理層層轉包黑產鏈
近日,安徽蕪湖“1·29”跨省非法傾倒固廢污染環境案一審宣判,浙江兩公司因污染環境罪被重罰1100多萬元,11名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法院同時對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作出一審判決。
此前,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矚目的“特大非法跨省傾倒有毒污泥案”進行了一審宣判。9名被告人共非法傾倒污泥約14800噸,污染土地修復工程總費用為1446.288萬元。數名被告人犯污染環境罪,分別被判處三年兩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還需支付生態環境修復費用。
《法制日報》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異地傾倒危險廢物案件時有發生。這背后的防治難點究竟在哪里?
利益驅動層層轉包
打擊力度亟待加強
從已經審結的案件來看,異地傾倒危險廢物已經形成產業鏈。
在江西省“特大非法跨省傾倒有毒污泥案”中,據九江市生態環境局副調研員王新明介紹,在2017年8月至2018年年初期間,犯罪嫌疑人舒某通過水路,將來自浙江杭州等地的約14800噸污泥運至九江市永修縣、廬山市、柴桑區等五地傾倒。
另據九江市公安局機動支隊二大隊隊長王剛介紹,這些人利用長江水道,通過層層轉包的形式,將發達地區各種垃圾非法運輸至欠發達地區傾倒,形成了一條黑色產業鏈。張某通過船運將污泥運至江西九江,以每噸105元的價格包給舒某,舒某等人將未經任何處理的污泥直接傾倒在九江的水源地附近。
“未經處理的污泥直接傾倒對環境的污染是比較嚴重的。”天津一家污泥處理公司的員工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這名員工解釋稱,未經有效處理的污泥會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泥經過雨水的侵蝕和滲透作用,容易對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還會造成地表水的富營養化。
“這樣的污泥還會造成土壤污染,其中含有的重金屬、大量病原菌、寄生蟲卵等會對環境和人類以及動物健康造成危害。當然,這樣的土壤不能再被耕種和使用,對周邊人群的生活環境也造成了臭氣污染。”這名員工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另據了解,一噸污泥無害化處理費用至少要在400元以上,而如果采取異地傾倒,成本僅僅每噸一兩百元甚至幾十元。
安徽省環保公益組織綠滿江淮項目經理張登高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異地傾倒危險廢物的企業多為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利潤有限,加之一些污廢處置公司出于經濟效益考慮,不愿意為其處理危廢垃圾或提高處理價格,更容易導致這些中小企業鋌而走險。”張登高說,近年來,一些地方也在進行設立暫存、搜集危廢物品公司的試點,希望改善非法處理危廢垃圾屢禁不止的局面。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環境法學院專家曹明德也認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相關案件頻發的主要原因。
“就異地傾倒污泥這一案件來看,污泥處理受托方的法律意識、環境保護意識明顯不夠。同時也可以看出在環境保護方面,法律的威懾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打擊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力度也需要不斷加強。”曹明德說。
據曹明德介紹,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對環境違法犯罪的認定已經不再要求必須有損害后果,只要排污行為達到一定標準就可以入刑。
“我國針對危險廢物的法律法規已經較為健全,不僅有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還有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等,均對非法處置危險廢物做出了相關懲處規定。相關法律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的經營活動。這意味著危險廢物不得擅自轉移、加工、處置,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3噸以上就可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要追究刑事責任。”曹明德說。
曹明德認為,針對異地傾倒危險廢物,各地有關部門、環境保護機構應該對企業、個人進一步普及環境保護法,加強環保法治教育,提高相關企業、個人的守法意識,使其明確違法后果,放棄僥幸心理。
異地傾倒監管困難
源頭治理刻不容緩
雖然異地傾倒危險廢物危害嚴重,但對其進行打擊治理仍面臨一些困難。
對于江西省“特大非法跨省傾倒有毒污泥案”,九江市生態環境綜合執法局負責人李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此案具有明顯的流竄作案、跨區域排污等特征,打擊難度大。”
據張登高介紹,一些中小企業的員工往往屬于跨省就業,給異地傾倒危險廢物提供了機會。“例如,家鄉在某省的員工會選擇去往另一省務工,其所在務工省份的企業會讓這些員工將危廢垃圾以一般固廢物品的名義,運輸至其家鄉較為偏遠的山區,這樣做就不容易被發現。”
“對于異地傾倒危險廢物這樣的行為,有關部門不可能全程監督,這屬于行政管轄中的薄弱環節。”曹德明說,“不法分子正是妄圖利用異地傾倒這樣跨轄區、跨省區的作案范圍,來鉆空子。這也說明監管查處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曹明德認為,在江西省“特大非法跨省傾倒有毒污泥案”中,因為某些小公司并不具備固體廢物處置資質,這才出現偽造審批公章,偽造相關營業執照、環保部門公章等作案手法。由此說明,哪些企業有排污需求,哪些企業能接手處置,當地環保部門應該對此有所了解,這是從源頭治理異地傾倒危險廢物的基礎工作。
據曹明德介紹,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轉移危險廢物的,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填寫危險廢物轉移聯單。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轉移危險廢物的,應當向危險廢物移出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移出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商經接受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同意后,方可批準轉移該危險廢物。未經批準的,不得轉移。”
“轉移危險廢物途經移出地、接受地以外行政區域的,危險廢物移出地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及時通知沿途經過的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曹明德說。
“申請、商請、批準和通知是法律對危害廢物跨省作業的四個法定要求,通過全程監管信息互通,實現污染預防。然而,異地傾倒黑色產業鏈在偽造證件后,不僅避開了監督,也把污染和風險也散布在傾倒途中。”曹明德認為,對此,需要抓住排污主體,通過掌握排污主體污染數據,實時監測污染物轉移數據。
近年來的媒體公開報道顯示,一些異地傾倒危險廢物案具有流竄作案、團伙作案特征。非法轉移傾倒工業廢酸、含重金屬污泥等危險廢物案件占比較多,并呈現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城市向農村,跨區域、規模化、團伙化轉移趨勢。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與管理系教授宋國君認為,目前對于異地傾倒危險廢物的行為缺少更加明確的法律規定,這是此類案件難以根治的原因之一。
“去年年底印發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中,雖然規定了對于單位或個人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的情況,政府作為權利人可以提起索賠,但未進一步說明具體的賠償金額、修復義務等。”宋國君說,為了更好地避免此類事件發生,可以出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專門法律或法規。
借鑒異地用警做法
發現問題就地查處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和第五十九條第一款作出修改。
張登高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工業固體廢物申報登記制度。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的單位必須按照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向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提供工業固體廢物的種類、產生量、流向、貯存、處置等有關資料。
“目前對于企業污廢的申報監管還不夠嚴格,尤其是對于污水、廢氣以外的污廢。”張登高認為,現有監管模式偏向于結果導向,還需要更多發揮企業自覺性,有關部門應該在這方面不斷完善監管。
曹明德認為,一些企業之所以鉆異地排污的空子,是因為存在雙重僥幸心理。“雖然法律規定了危險廢物轉移聯單制度,但受管理權限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束縛,加上違法者往往選擇偏僻地區傾倒,且多在夜間行動,讓監管部門防不勝防。同時,一些實施異地傾倒危險廢物的企業自認為即便被發現和查處,監管部門也只能查到運輸者、處置者,他們還有機會逍遙法外。”
宋國君建議,從源頭上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需要遵守、執行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對于此類異地傾倒危險廢物事件,除了對異地傾倒危險廢物行為的實施者提高處罰標準,也要讓產生危險廢物的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不僅要承擔連帶民事賠償責任,而且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企業在將危險廢物委托給處理商后,必須了解危險廢物處理動向,徹底杜絕此類層層轉包的黑色產業鏈。相關企業要認識到,承包處理危險廢物是一種商業行為,在運到指定的危廢處理場所后要出示回執,生產企業也要像環保部門申報。”宋國君說。
曹明德認為,除了違法主體之外,危險廢物產生地的監管部門也要切實擔起責任,避免出現監管漏洞。對轄區內污染物的數量、流向、處置措施等實行全天候監管,要建立清晰的臺賬,對轉移危險廢物實施轉移聯單制度,敦促企業依法依規排污,對違法行為決不縱容。異地傾倒危險廢物屢禁不止,與地方保護主義不無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流出地對此失察甚至縱容所致。對此,環保執法可借鑒“異地用警”的做法,采取環境監察異地執法,發現問題就地查處,這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保護主義。
就訴訟環節而言,曹明德說:“以江西‘特大非法跨省傾倒有毒污泥案’為例,九江市政府作為訴訟方,代表著公眾利益,這樣的訴訟是一種公益訴訟。目前一審結束,在之后的審理程序中,可以把環境組織、非盈利環境保護社會組織等吸收進來,考慮將其作為第三方共同訴訟人。”(記者 杜 曉 實習生 鄧清月)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