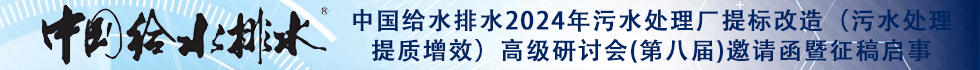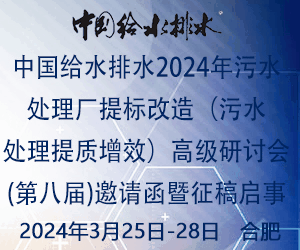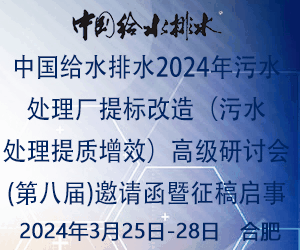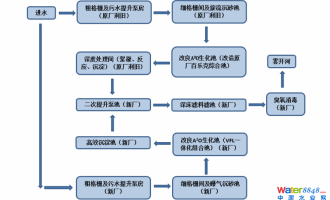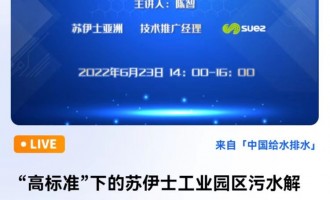呂忠梅:“繼續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高頻率監督領域”
來源: 南方周末客戶端 2024年03月05日
目前,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已正式啟動。可以說,這個議案中提出的意見建議得到了完全采納。
如果在生態環境檢察工作中,依然各干各的,互不來往,就會出現應該在行政、民事、刑事檢察工作中發現的公益訴訟線索發現不了,或者發現了線索但在辦案過程中因證據收集、起訴準備等不協同而影響案件辦理的公正與效率。

2023年11月,呂忠梅在浙江大學、浙江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的活動上發表演講。(圖片來源:中國農工民主黨官網)
與北京人民大會堂隔了兩條街,坐落于西交民巷的全國人大機關樓莊嚴大氣。
一年前,呂忠梅在這里有了一間自己的辦公室。這位曾連任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法學學者,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后,有了一個更特殊的身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一路走來,身份在變,但呂忠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不變。1984年,她將環境法作為學士學位論文選題,次年進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院環境法專業研究生,畢業后到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任教。1996年,呂忠梅在調研中發現,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她開始為長江立法奔走呼吁。
2003年,呂忠梅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后連任第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2018年到2023年,呂忠梅任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二十多年來,環境保護法的修訂、民法典中寫入以“綠色原則”為核心的綠色條款、長江保護法的出臺,在多部法律的立法過程中,都能聽到她的聲音。
2024年2月23日,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圍繞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的相關話題,南方周末記者專訪呂忠梅。
依然保持高頻態勢
南方周末:2023年10月,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關于打擊環境犯罪和加強環境司法能力建設的專題詢問會上,你作為代表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問,像這樣的活動是第一次參加嗎?
呂忠梅:我不是第一次參加全國人大專題詢問會。我從擔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開始,便多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參加過幾次專題詢問會并提問。
南方周末:近年圍繞環境問題,全國人大的監督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
呂忠梅:專題詢問是人大監督的一種形式,人大監督還有聽取國務院和兩高報告工作、開展執法檢查等多種形式。自我擔任人大代表以來,環境保護問題一直是人大監督工作的重點領域。我記得十屆全國人大最早舉行的專題詢問,就是有關污染防治方面的問題,每年也還會安排一些環境保護領域的執法檢查。尤其是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向同級人大報告環境質量狀況和環境保護工作情況,接受人大監督。這是對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環境保護工作的常態化制度安排。從全國人大的監督工作看,每年4月份的常委會聽取國務院報告全國環境質量狀況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情況已經持續了16年;每年安排對一到兩部相關法律的執法檢查,結合執法檢查安排專題詢問,已經形成機制。
比如,202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安排了三項有關監督工作:一是4月份聽取并審議國務院2022年度全國環境質量情況和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的報告,由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工作報告;二是10月份圍繞打擊環境犯罪和加強環境司法能力建設聽取“一府兩院”的專題報告并開展專題詢問;三是在10月份的常委會會議上,還聽取和審議了“關于濕地保護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內容是對濕地保護法實施一年來的情況進行法律監督。
就專題詢問這種監督形式看,不僅詢問的范圍不斷擴大,詢問方式也在不斷發展。比如,2023年10月份的專題詢問,是第一次圍繞一個主題,同時對“一府兩院”進行專題詢問,詢問的深度和廣度都比過去有了加強,也是一個創新。
南方周末:我們能否認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在履職第一年,繼續選擇與生態環境相關的主題進行專題詢問,這個時間點具有一定的特殊意味?
呂忠梅:2023年是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履職的第一年,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年聽取并審議國務院報告并開展兩次執法檢查的基礎上,選擇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專題詢問并進行創新,表明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僅繼續把生態保護作為高頻率監督的領域,而且顯現出更加創新監督內容和方式的態勢,是貫徹落實 “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新舉措。
促進“四大檢察”融合履職
南方周末:2023年6月全國人大公布的年度工作計劃里,有關環境保護領域的監督工作有3項,其中之一就是對“一府兩院”的專題詢問。這項準備工作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呂忠梅:2023年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年度工作計劃就要確定準備工作的時間進度和責任單位。根據工作安排,對“一府兩院”的專題詢問,由監督司法委員會牽頭、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參與。應該說是從準備專題詢問的調研和會議方案開始,我就參與了相關準備工作。因為環資委的工作領域是環境資源立法及其監督,監司委的辦事機構與環資委的辦事機構也就相關工作進行了充分溝通。2023年7月到9月,我也專門和環資委的同志們到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進行了調研,我還到陜西、內蒙古等地進行了調研,跟蹤了解環境司法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陜西的調研,在實地察看、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的基礎上,形成了專題調研報告;內蒙古調研時,邀請“兩高”和東西部地區十多個省份的法院檢察院分管領導就加強環境司法能力建設進行了專題研討,對存在的問題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達成共識。
南方周末: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職能中,都涉及保護生態環境的工作。為什么專題詢問時,“四大檢察”發展的不平衡會成為向應勇檢察長提出的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對于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呂忠梅:我作為環境資源法的研究者,關注環境司法問題已經有許多年。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成立之初,就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研究中心的學術委員會主任。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帶領學者和環境司法實務工作者,每年在調研基礎上形成《中國環境司法報告》并向社會公開發布。我主持報告的撰寫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經過多年的跟蹤研究,對于中國環境司法的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比較全面的專業判斷。
這次專題詢問會上,把提問機會留給這個問題,是因為無論是從我們的長期跟蹤研究中,還是監司委為準備這次會議而進行的專門調研中,都認為“四大檢察”發展的不平衡已經成為影響生態環境檢察職能發揮進而影響生態環境司法工作的一個問題,迫切需要從加強能力建設的角度盡快加以解決。
南方周末:所謂“四大檢察”發展不平衡有什么具體表現?
呂忠梅:形式上表現為環境資源領域的刑事檢察、公益檢察案件多,民事檢察、行政檢察案件少;工作機制上表現為協同性、聯動性不夠;工作能力和水平難以適應生態環境領域檢察官具有法律與科技復合型知識體系、跨法律學科的理論功底、綜合處理不同法律性質案件的履職能力等。
舉個例子吧,在公益檢察領域,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從最初的90%到現在50%以上,始終在公益檢察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與食品藥品安全、消費者保護、國有資產保護等相比,不僅有超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特殊性;而且一個違法行為可能在引起行政違法、環境犯罪、民事侵權等私益訴訟的同時,引發公益訴訟,形成兩種甚至是三種不同訴訟的“結合”,比如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都會需要將過去分工明確的行政檢察、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與公益檢察工作打通,形成協同辦案、一體履職的格局。
如果在生態環境檢察工作中,依然各干各的,互不來往,就會出現應該在行政、民事、刑事檢察工作中發現的公益訴訟線索發現不了,或者發現了線索但在辦案過程中因證據收集、起訴準備等不協同而影響案件辦理的公正與效率,更嚴重的是不同訴訟的裁判結果對當事人的權利剝奪或給付義務疊加,導致“一事多罰”,不能在個案中妥善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影響社會公平正義。
因此,“四大檢察”平衡發展、一體履職,對于檢察機關依法履職,保障和促進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我也很高興地看到,應勇檢察長在回答詢問時不僅直面這個問題,并對出現問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也提出了明確的促進“一體履職”工作思路。我相信,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以系統觀念和整體思維謀劃生態環境檢察工作,一定能夠實現“四大檢察”工作的協調互補和統籌聯動。
一條理想的法律人之路
南方周末:作為高校的學者到法院任職,再到政協和人大工作,這些工作崗位的變動,對于環境法專業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尤其是對環境法治的認識和推動,是否會因工作崗位、工作內容、工作節奏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呂忠梅:我1984年北大畢業到法學院教書,2000年到湖北省高級法院任副院長,2003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2013年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2015年調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2023年任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我作為一個法律人,走過了從學者到法官,從研究者到管理者,從見證者到執行者的人生歷程。
這些年來,雖然工作性質、工作崗位不同,工作內容也有巨大反差,但這些不同不僅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更重要的是為我提供了將自己的學術理想和研究成果轉化為法治實踐巨大舞臺。
現在再來看,我雖然經歷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始終沒有離開法律專業領域;雖然不同性質的工作崗位涉及不同的工作納入,但都為我提供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觸摸實踐中的真實、聽到不同聲音的條件與機會,能夠讓我看到校園中學者看不到的情況、獲得他們無法收集的資料、思考他們想不到的問題,并且還有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在立法決策、司法裁判、民主監督等過程中直接表達出來的機會。
所以,我經常會想,對于一位法律人而言,我走過了一條最理想的人生之路:經歷了從法學理論研究到立法、司法實踐的全過程,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推動法治的發展作出直接貢獻。
南方周末:過去一年在人大的工作,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大的變化嗎?
呂忠梅:從形式上看,的確有一些變化,比如從人大代表到人大常委會委員、專委會副主任委員,辦公室也搬到了全國人大機關。但從實質上看,不應該也不可能有大的變化。我的專業領域是環境法學,無論在哪個單位、在哪個崗位,研究環境法理論、推動環境法治實踐都是我的工作核心,不會變化。
過去,我以學者、代表、委員等身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立法、司法、執法實踐,比如推動環境保護法的修訂、推動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環境資源審判庭、推動制定長江保護法、推動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等等;現在,我以人大常委會委員、專委會委員身份,以更加直接的方式繼續這些工作。
到全國人大環資委工作這一年來,我參與了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年度工作計劃的制定、參與了環資委的工作計劃制定;也直接參與了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制定、海洋環境保護法和礦產資源保護法的修訂等重要的立法工作,參與了濕地保護法的執法檢查,也參加了國際會議、參與多場議會外交活動。在生態環境立法、監督和環境外交等多個方面,收獲滿滿。
南方周末:202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啟動環境法典編纂研究納入年度工作計劃,但未正式啟動立法工作。2023年的一次會議上領銜提交“將環境法典編纂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議案,又提出專家建議框架后,這個議案被采納了嗎?
呂忠梅: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將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納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一類項目及2024年立法計劃。目前,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已正式啟動。可以說,這個議案中提出的意見建議得到了完全采納。
南方周末:工作上接下來還有什么打算嗎?
呂忠梅:法典編纂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僅僅是編纂法律條文,在編纂前及編纂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理論論證和對現行法律如何進行體系化的方案研究;在法典編纂完成后,還會涉及法典解釋、與法典相關法律的修訂、法典的司法適用等一系列問題。因此,現在和未來的相當長時間內,我都會圍繞法典編纂,展開相關工作,這些足夠做10年甚至更長時間了。(蔣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