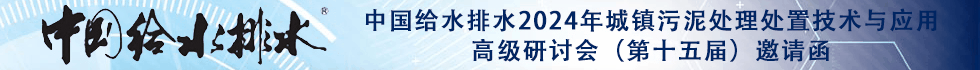“海綿城市”在這里發芽
在國內不少發達城市仍為如何實現避澇焦頭爛額時,深圳光明新區卻跨得更遠。他們所實施的低影響開發理念,對于攻克“逢雨必澇”的城市頑疾具有啟蒙意義——“海綿城市”已經在這里生根發芽。
有人說,環顧深圳一周,便閱讀到這座國際都市的發展簡史。與市區高樓鱗次櫛比不同,成立于2007年、位于西北之隅的光明新區,至今仍些許彌漫著改革發展初期的味道。很多生活在關內的人到此會有這般恍惚,認為與大都市的格調不符。但在某些領域,光明新區的理念和成就已穿過時間縱軸,站在深圳乃至全國絕大多數發達城市之前。
低影響開發“有形亦無形”
都說“中國城市如何應對降雨”長期無解,那么光明新區做了什么?他們正做的不是避澇,而是把水留住并利用,構筑出當前被各方熱議的“海綿城市”之雛形——被業界視為突破傳統理念的新思路。
光明新區公園路,常人眼中和其他道路并無二致,但在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任心欣眼里卻視為杰作。
“在自行車道和人行道鋪設了透水瀝青和透水磚,下面不是水泥砂漿的不透水層,而是采用厚度15~20厘米的砂層和卵石墊層。它們孔隙率很高,能鎖住大量雨水,在雨后緩慢滲透至土壤。”任心欣說,“中間綠化帶的設計也有講究。綠化帶兩側設有下凹綠地(植生滯留槽),比路面低15厘米左右。這樣,車行道的雨水可通過路牙的孔洞匯集進來,然后儲存在土壤層中并得以滯留和凈化。”
這就是一項極其典型的、被稱為低影響開發雨水綜合利用(簡稱“低影響開發”)的設施。它被證實能有效提高雨水資源利用率,緩解城市洪澇災害頻繁暴發、徑流污染等突出矛盾。今天,這類設施正在光明新區的道路項目中發揮功用。氣象資料顯示,深圳每年降雨次數超過100場,采用低影響開發設計的路段可完全消納每場25~30毫米的降雨量,將七成雨水留在道路紅線內,不再外排。即便應對降雨量超過100毫米的極端天氣,亦能發揮一定的緩滯、削峰作用。
除了道路,低影響開發在公共建筑和公園等類型項目中同樣成效顯著。監測數據表明,前者能夠留存的降雨約六成,而后者這一比例更高達85%。
距公園路兩公里以外,物業管理經理夏生高也自認為受益于低影響開發。他的工作地點——光明新區群眾體育中心的屋頂鋪滿綠油油的草坪。每逢降雨來臨,都將透過上萬平方米的草坪凈化,同透水鋪裝的廣場匯集的雨水共同貯存在占地500平方米、容積達750立方米的地下蓄水池中。經過凈化,這些雨水可滿足保潔和綠化帶澆灌需求,年利用量超過1萬立方米。
“系統處于全自動運行模式,所用電費比節省的水費劃算很多。雖然樓頂草坪需定期修剪,但說不上多難。”經驗老道的夏生高雖是首次接觸這一創新,卻不吝惜溢美之詞來打消眾人對于運營環節的疑慮。
群眾體育中心羽毛球館屋頂綠化疊加自然采光通風的設計,還帶來可觀的附加值——省去中央空調系統,為建設者削減大幅設備投資。夏生高說,這里空氣流動性很好,即便遭遇三伏極端天氣也無大礙,多數時候都非常舒服。“屋頂綠化功不可沒,否則不裝空調怎么行?”憑借其經驗判斷,屋頂綠化足以有五六攝氏度的降溫效果。
“對比常規項目,部分低影響開發項目會有強烈的直觀感受,但多數并不能引起普通人注意。不過我們通過監測和評估,這些項目的環境和生態效果都很好。”任心欣信心滿滿。
協調合作是關鍵
常人看來,低影響開發不算高科技,那實施關鍵與難點何存?光明新區城市建設局(以下簡稱“城建局”)水務科姚濤身為政府與市場的聯絡者,他表示,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投資,造價是所有人的疑慮焦點。
不過這在專業人士眼里“不叫事兒”——采用低影響開發的項目從成本增量的角度看幾乎可忽略。即便光明城高鐵站前的道路項目選用了昂貴的排水型瀝青路面,比普通瀝青層增加超過60%的成本,其總造價增幅不過2%。
真正的困難,在于協調與合作。城建局副局長馮韶輝指出,這類尚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如何自上而下厘清并協調好各種關系、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機制,才是低影響開發最終能否融入項目、科學推進直至最終落實的根本。這里既包括政府決策取得共識,也包括下游各專業和實踐環節步調一致,“要將各部門、各專業擰成一股繩”。
過程坎坷,光明新區已身先垂范。據介紹,為確保低影響開發雨水綜合利用示范區創建工作順利實施,深圳市政府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分管副市長和光明新區管委會主要負責同志擔任召集人,由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市財政委員會、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市人居環境委員會、市水務局、市監察局、市審計局、市住房和建設局、市城市管理局等單位主要領導擔任成員。去年7月,以新區管委會名義印發的《深圳市光明新區建設項目低沖擊開發(低影響開發)雨水綜合利用規劃設計導則實施辦法》還用地方性法規政策的方式,確定了各部門職責和審批審查程序。
“如果不是市政府牽頭,恐怕很難推進。”即便是技術人士,任心欣亦持同樣觀點。一種新型理念引入之初,分歧在所難免,主要源于傳統理念的束縛、標準規范的缺失以及政策保障機制不盡完善。馮韶輝說:“我們經過反復培訓、合作和溝通,與規劃、國土、交通、水務、城建、城管等部門很快達成共識,總體來說比較順利。”
如果說政府層面達成共識尚且容易,那么工作越向下延伸,分歧甚至沖突就愈加劇烈。以至于記者的疑問話音未落,任心欣的答案已脫口而出。
“多專業合作在設計層面存在很大困難。最簡單的例子是,園林專業原先設計綠地無須過多考慮保水、蓄水、滲水等問題,養護環節也非常簡單。實施低影響開發設計后,養護難度增加了,植物搭配也受到局限。”任心欣說,“現在通過協調機制的建立、強化專業溝通,不同類型項目中,給排水專業已能與建筑、結構、路橋、園林等專業展開充分合作,共同落實低影響開發理念。”
與設計相似,后期施工及管養等環節同樣會屢遭磕絆。“雖然不牽扯高科技,但工序復雜便容易遭遇抵觸,這很棘手。”不過,馮韶輝堅信成事在人,凡事只要戮力同心,就沒有過不去的檻,“要堅持統籌安排、科學謀劃、部門合作的機制,必須做到規劃先行,從土地出讓階段開始,將低影響開發理念貫穿始終。”
全面推廣有條件
多年堅持,光明新區在低影響開發領域成績卓然。這對于攻克“逢雨必澇”的城市頑疾具有啟蒙意義——“海綿城市”生根發芽不是夢。
“我們原先也僅限于排水、留水的零散做法,后來在住建部領導勉勵和指引下,終將其整合成系統,而一旦形成規模,效果更明顯。”馮韶輝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光明新區有些理念很超前。”
成就讓光明新區在圈內備受贊譽,更讓不少省市產生興趣甚至心生艷羨。去年末,住建部在合肥舉辦基礎設施建設典型經驗交流會之后,馮韶輝和任心欣的日程更加忙碌起來——除了屢次進京向住建部領導匯報和溝通有關進展,還要接待各地取經團,或是被請到其他城市交流經驗。
同時作為國家水專項“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綜合示范與評估”課題負責人之一,任心欣看好低影響開發在國內的前景以及可能帶動整條產業鏈發展的潛能。她希冀更多人關注這項事業并集思廣益,思路和形式會愈加豐富。任心欣認為,《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構建(試行)》的導則出臺及時而必要,為更多省市提供了參考依據。它最大的意義是定方向而非手段,“用總體目標來考核最科學”。
但她警示,廣義講低影響開發理念強調對原有自然水文循環的保護適用于所有城市,但針對不同地區,其應用出發點與具體技術措施都有較大差異。各城市應根據降雨、土壤、水系、城市建設特點開展目標制定和技術措施篩選,充分尊重當地水文條件等實際因素。
“絕不能一哄而上,必須進行本土化改良,設置好目標、配套好政策、展示出特色。”馮韶輝重復。
時至今日,深圳光明新區關于低影響開發的探索仍在繼續。隨著制度和程序逐步清晰,推進重心正向技術和應用層面轉移。他們正全面鋪開包括居住社區、工業園區、舊改項目等更多類型的低影響開發應用,并籌劃優化已建的示范項目,“舉例來說,滲水瀝青固然好,但在車流量大的地區容易結構破壞,所以未來會變更設計。而光明新城公園內部分陡坡的草溝,起初并未考慮水流速度過快的問題,現在看水土保持效果不佳,改造時會增設堡坎分級緩滯。”
技術探索長期且無止境,背后要有政府鼎力支持。據透露,光明新區城建局已與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達成合作意向,后者將組織專家特別是外國知名專家做技術后盾。城建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光明新區已進入低影響開發建設第二階段的收官之年,即在第一階段工程示范基礎上完成機制構建。在即將到來的第三階段,他們將完善配套政策并運用獎懲等經濟手段,在建設項目中推廣低影響開發雨水綜合利用并全面建成低影響開發示范區,“到2020年,新增的適宜建設項目全部合理開展低影響開發雨水綜合利用”。
但眼下仍有現實問題亟待解決。例如,政府在低影響開發標準體系和參考標準方面尚存空白,以致財政部門資金撥付常常無章可循,這讓人感到為難。此外,雖然2012年光明新區城建局作為參與單位申請了國家水專項課題的科研資金,僅能滿足科研需求,對于未來更大規模示范項目建設來說,資金保障機制缺乏,地方財政更是權宜。
“未來一定要引入社會資本,這并非全是經濟考慮,更是社會和生態價值之體現。我們希望,國家有關部委可參考綠色建筑等級評定進行資金支持,與社會資本引入過程相輔相成,讓補貼標準有章可依。”對于下一階段工作前景,馮韶輝坦言并無太大壓力,“如果說一定有,那就是來自各方的期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