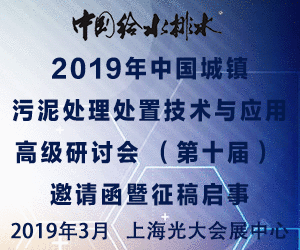摘要:我國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行業的PPP(政企合作)近期不斷有政策出臺,相關試點亮點頻頻。在企業方面,某些水務企業希望通過PPP來進行資本和經營的擴張,而不少投資人也希望從中尋到商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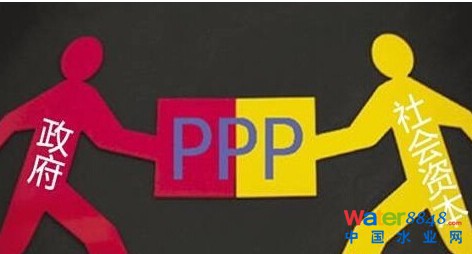
PPP模式——政企合作
我國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行業的PPP(政企合作)近期不斷有政策出臺,相關試點亮點頻頻。在企業方面,某些水務企業希望通過PPP來進行資本和經營的擴張,而不少投資人也希望從中尋到商機。
然而,業內人士指出,作為水務企業,如果單純希望通過PPP擴大資本數量,則難以彰顯政企在合作建設基礎設施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務的初衷。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水務企業都應該捋順資本、效率、責任方面的關系,既能夠通過PPP讓公眾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務,又能讓資本在這一模式中發揮效用,讓企業獲得長期穩定合理的經濟回報。
城市水務行業引入PPP的主要目標,首先是提高經營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務,而非單純擴大資本數量
由于資產成本勢必要用即期或遠期的現金流量來覆蓋,前端過量資本進入,必然會給之后的消費價格或公共財務形成壓力
如何使在競爭中獲得市場的企業能在市場中維系競爭狀態,防止其濫用市場獨占權利,是目前水務行業PPP過程中的難點
重慶唐家沱污水處理PPP項目談判中,政府更為關心的是,如何設計出一個有效的價格機制,來管控企業在整個特許經營期內可能發生的價格壟斷,并向企業的價格行為施加競爭壓力,包括采用“利潤率限定”、“價格封頂或包干”、同域、同業“價格比較”等方法
在重慶北部片區供水PPP項目談判中,根據公用事業“普遍服務”原理規定,企業享有獨家經營的權利,但與此同時,它必須“保證向服務區內一切愿意接受服務和愿意支付服務價格的人提供連續、充足和有質量的供水服務”
城市水務行業無疑再次成為此輪PPP潮中的一個熱點,與其他公共服務行業相比,主要包括自來水和污水處理在內的水務行業屬于典型的區域自然壟斷行業。
在我國城市水務行業以往某些PPP實踐中,盡管在打破傳統的國有或行政壟斷方面有了一些突破和改善,也引進了一些社會資本或境外資本,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沿襲著行政決定的方式。
如果我們期望通過城市水務行業的PPP過程孕育出真正和有實力的自然壟斷者,首先應該使水務行業的PPP過程脫離行政壟斷的軀殼而回歸市場競爭。
效率目標是關鍵所在
首先是提高經營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務
而非單純擴大資本數量
城市水務行業屬于資本密集性行業,其PPP過程中肯定涉及大量的資本運作。但水務行業PPP項目在瞄準融資功能和融資數量時,是否還有別的目標?面對在我國若干城市水務行業政企合作資產大幅溢價的情況,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首先,一方面,我國的城市水務企業大部分都在微利、保本經營甚至虧損,但另一方面,其資產卻在超出原值數倍甚至十幾倍出售。這一悖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次,溢價收益去了哪里?第三,溢價成本的最終埋單人又是誰,即資產溢價轉讓與今后的價格或公共財政支出有無關聯?
比如,某城市以數倍于原值的價格出讓了本地的水廠資產。事后企業要求依據其投資成本調整水價或增加補貼,“溢價”成了“提價”。水務資產的大幅增值,如果導致公眾的消費價格或公共財政補貼隨之水漲船高,那么,這種溢價無非是價格透支或寅吃卯糧。因此,過度關注PPP的融資功能,或將融資數量作為衡量績效的唯一目標,甚至試圖把PPP作為撬動資本或收益無序擴張的杠桿,那么,PPP就變成了“圈錢”的工具。
城市水務行業引入PPP的主要目標,首先是提高經營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務,而非單純擴大資本數量。由于資產成本勢必要用即期或遠期的現金流量來覆蓋,前端過量資本進入,必然會給之后的消費價格或公共財務形成壓力。如果僅僅關注前端融資的受益人,而不關心后端成本的埋單人,終將釀成惡果。
從這個意義上講,對PPP績效的考量,不能忽視公共服務效率、質量、范圍、價格或對公共福利的改善和增加程度。
價格怎樣管控?
應設計出有效的價格機制
在整個特許經營期向企業的價格行為施加競爭壓力
城市水務行業的PPP經常涉及特許經營競爭過程,競爭包括很多內容,其中最難的是對價格競爭的判斷。
眾所周知,水務特許經營通常涉及一個較長的時段,如15年~20年時間,甚至更長。目前還沒有哪一個企業能夠或敢于對整個特許經營期進行一次性競價,往往都是對特許經營起始期(3年~5年)進行競價。
對資金實力雄厚的企業來說,往往采用“先虧”的辦法,用較低的起始報價擊敗其他競爭對手,來贏得特許經營權。等到起始年限過后,企業作為地位穩固的壟斷者再與政府討價還價。
這種由當初被動的競爭者變為之后的主動壟斷者、由市場進入時的“競爭價格”演變為市場占據后的“談判價格”的過程,已成為監管窘境。因此,如何使在競爭中獲得市場的企業能在市場中維系競爭狀態,防止其濫用市場獨占權利,是目前水務行業PPP過程中的一大難點。
有鑒于此,在筆者2006年參與的重慶唐家沱污水處理PPP項目談判中,政府并沒有過度關注企業的起始報價水平,相反,更為關心的是,如何設計出一個有效的價格機制,來管控企業在整個特許經營期內可能發生的價格壟斷,并向企業的價格行為施加競爭壓力,包括采用“利潤率限定”、“價格封頂或包干”、同域、同業“價格比較”等方法。
譬如法律文件的價格章節中可以規定,如果結算價格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后,與同區域其他同類企業相比失去競爭性,明顯高于同行業平均水平,則需重新核定結算價格等。在PPP項目實踐中,設計出一個科學合理的價格管控機制非常重要。
界定合法成本與合理成本邊界是難題
應該防止企業以成本
合法性掩蓋成本的不合理性
對于PPP過程中的“合法成本”與“合理成本”問題,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是“成本作價”+“利潤率限定”的價格模式。例如,我國《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將企業的利潤率限定在8%~12%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無法期望通過提高利潤率來增大利潤總額,因此,蓄意擴大成本規模就成為一個既合法又有效的途徑。例如,一個500萬元興建的水廠,當利潤率限定在8%時,允許的利潤額為40萬元。如果企業將投資“蓄意”擴大到1000萬元,并以此作為成本基數來計算利潤留成,這時人們發現,企業最終還是堂而皇之地獲得了80萬元的利潤,同時也沒有違反限定的利潤率標準
——然而,此時消費價格卻上漲了不止一倍的水平。這就是合法成本與合理成本之間的沖突。
在成本作價和利潤率限定的情況下,企業具有擴大投資成本的強烈動機,即以合法成本來攝取不合理的利潤。以成本之水抬升利潤和價格之船。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界定合法成本與合理成本的邊界,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合法成本與合理成本之間,始終存在矛盾。企業為此進行成本投機繼而達到利潤投機的路徑很多。比如,政府可以出具的特許經營授權文件中明確規定:企業應當本著節約成本的原則進行合理、適度的資本性和經營性融資,其融資成本應不高于同期當地銀行的平均條件、嚴格限于直接生產和服務。合作公司所需采購設施數量、質量、價格和工程建設成本應當不高于同行業的可比較的合理水平。“企業內部的薪酬調整,如果不對現行審定的水價成本造成影響,則由企業自行確定”等條款的制定,目的就在于防止成本合法性下掩蓋的成本不合理性。
政府對水量兜底是否合理?
企業享有獨家經營的權利,前提是它必須保證
向服務區內提供連續、充足和有質量的服務
從風險控制的角度審視,PPP的一大特點就是改變了公共服務投融資、運營和管理的傳統風險配置。通過合作使得風險分散,并由合作各方分擔或共擔。
然而在我國城市水務行業以往的某些PPP項目中,“風險共擔”原則經常得不到很好地履行。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政府為PPP企業的某些風險進行兜底。
例如,一些企業經常要求政府先行確定和審批服務水量,并在實際處理量達不到既定規模時,政府需要保量購買。反之,如果按照審批的規模建成的設施能力滿足不了實際需求,企業無需承擔責任。
在我國以往的某些水務PPP項目中,企業一方面希望享有獨家經營權利,另一方面卻不愿獨家承擔投資和運營風險,由此一來,本應由企業承擔的市場風險中的幾個關鍵方面——競爭風險、投資風險和運營風險,就隨著政府審批和政府兜底實現了轉移。
在重慶北部片區供水PPP項目談判中,根據公用事業“普遍服務”原理規定,企業享有獨家經營的權利,但與此同時,它必須“保證向服務區內一切愿意接受服務和愿意支付服務價格的人提供連續、充足和有質量的供水服務”,這也是政府不再審批其他企業進入服務區域的重要前提。
重慶唐家沱污水處理PPP的法律文件也明確規定,企業的服務應“符合城市總體規劃,滿足特許經營區域內日常需求,以及具備適度的儲備能力”。換言之,企業應該根據服務區域的人口現狀和增長趨勢、城市發展規劃、平均用水量、峰值用水量等因素去合理預測、建設、改造設施規模,應具備一定數量的儲備能力并承擔相應的投資和運營風險。政府允許適度的儲備能力建設費用計入固定成本,但日常的經營性付費則必須根據實際發生的處理水量來計算,政府拒絕進行水量兜底。
除了“普遍服務”原理外,西方公用事業法中還有另一條原理——專營服務區域內的“強制延伸服務”,即企業必須履行向服務區域內新增的服務人口提供延伸服務的義務。
由此看來,無論是普遍服務原理還是強制延伸服務原理,都蘊含著一個基本原則:作為特許獨家經營的企業,必須向專營區域內所有愿意接受服務和愿意支付價格的公眾提供充足和連續的服務,并應承擔相應的投資和運營風險。
反觀我國城市水務行業以往PPP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尤其是對服務水量的保底,是有悖上述基本原理的,既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符合“利益分享/風險分擔”的原則。
水務行業拓展PPP別忘初衷 改善服務是首要目標
發表于:2015-3-26 來源: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