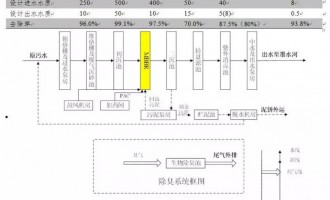“根據(j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精神,環(huán)境保護工作今后也要突出市場作用,以更加成本有效的方式來解決環(huán)境問題。”中國科學(xué)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xué)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xué)院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組組長王毅說,這一路徑,《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十分明確。
“三中全會關(guān)于生態(tài)文明的論述,與之前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關(guān)于生態(tài)文明、空間格局、資源效率、制度建設(shè)等論述是連貫的。”王毅說,“往前更進了一步,有助于推動環(huán)境保護工作,也更多地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相關(guān)。”
王毅是在11月16日召開的“重塑藍天:空氣質(zhì)量管理國際研討會”上向記者作出上述表示的。
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我國環(huán)保工作過去一直以行政手段為主,市場為輔。市場方面的政策相對不足。此次,《決定》中關(guān)于自然資源產(chǎn)權(quán)制度、生態(tài)補償?shù)龋寂c經(jīng)濟體制改革直接相關(guān)。
“首先將自然和生態(tài)資源資產(chǎn)化,這樣一來,無論是開發(fā)、保護或者交易,有了可衡量的價值標(biāo)準(zhǔn),就可能用市場化的手段處理。”王毅說,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可以更有效地觸及更多領(lǐng)域。
“《決定》強調(diào)了市場的作用,并向環(huán)境保護領(lǐng)域釋放了市場化的正面信號。”公眾環(huán)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我們對這一大方向很認同。”
“自然資源產(chǎn)權(quán)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市場化需要的制度。”環(huán)境保護部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夏光說,過去,對環(huán)境、生態(tài)等公共自然資源系統(tǒng),不太注重確定其產(chǎn)權(quán)。而對于這些公共的無主資源,容易出現(xiàn)過度使用的情況,這時候提出對自然資源的產(chǎn)權(quán)界定很有意義。比如大氣資源,由政府做公共管理,同時也可以劃分為很小的單元,認定主體,對單元大氣環(huán)境質(zhì)量負責(zé)。大氣污染物減排就是如此,根據(jù)區(qū)域大氣環(huán)境容量資源,分配排放權(quán),通過市場化交易體現(xiàn)價值。
“根據(jù)國際經(jīng)驗,對大氣、水域等自然資源通過產(chǎn)權(quán)界定以后,將使用自然資源的收益和責(zé)任聯(lián)系在一起,實現(xiàn)主體承擔(dān)。”夏光說,比如,通過制度安排,將一個湖泊委托給一個市場主體,可以開發(fā)利用來賺錢,但不能破壞環(huán)境質(zhì)量,這樣的話,市場主體就有動力去開發(fā)利用,也有興趣和各種污染現(xiàn)象做斗爭,拒絕他人排放污染物。
政府不出面,通過市場主體去維護良好環(huán)境狀態(tài),有利于調(diào)動很多社會主體參與保護和利用。搞好自然和環(huán)境資源產(chǎn)權(quán)制度,可以把政府主體變成社會市場主體。之前的類似改革,實踐最多的是林權(quán)改革,過去森林國有,國家護林,農(nóng)民往往成為“對立面”,而通過林權(quán)改革,把森林分成一片一片,劃歸農(nóng)民所有,農(nóng)民就有權(quán)、有動力去護林,因為有收益。
“市場需要更加有效配置資源,一定的成本應(yīng)得到更好的效果,避免高成本實現(xiàn)目標(biāo)。”王毅說,“要更多地依靠市場,以更加成本有效的方式來解決環(huán)境問題。”
“目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源定價不完善。”馬軍說,排污者并沒有真正為污染影響付費,加上監(jiān)管不嚴(yán),最終形成了大量的高耗能產(chǎn)業(yè)。“如果能理順關(guān)系,比如確定生態(tài)紅線并真正守住,合理確定資源價格并切實執(zhí)行,從根本上促進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霧霾、水、土壤等環(huán)境問題才能逐步解決。”
強化制度建設(shè),保障發(fā)揮市場作用
“生態(tài)文明的制度體系還有另外一個方向。”夏光說,“就是強化政府的管制,由國家代表公共利益進行管理。”國家有責(zé)任保護后代利益,需要給予制度保障,比如劃定生態(tài)紅線,實行獨立監(jiān)管,加強政府權(quán)力等政策。“這和市場化不矛盾,是實現(xiàn)生態(tài)文明的兩個途徑。”
過去對國土功能沒有細化規(guī)劃,現(xiàn)在有了主體功能區(qū)規(guī)劃;過去對生態(tài)功能區(qū)域沒有劃定,現(xiàn)在有了生態(tài)紅線。“宏觀上確定了人類活動的上線和生態(tài)保護的底線。”夏光說。比如,劃定一個湖泊,大的保護原則由國家和政府層面確定,至于什么方法,則是技術(shù)性問題,由市場去做。
“單靠市場或單靠政府制度都不夠,必須兩方面并行。”夏光說,對于制度建設(shè),《決定》強調(diào)了3個關(guān)鍵詞。一是“生態(tài)文明的制度體系”,二是“系統(tǒng)完整”,三是“加快”。這是學(xué)習(xí)領(lǐng)會三中全會精神的關(guān)鍵詞。
“制度體系”強調(diào)的不是一兩項制度,而是一系列制度的總和。
“系統(tǒng)完整”強調(diào)生態(tài)系統(tǒng)之間是相互聯(lián)系的,各個要素形成一個鏈條。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關(guān)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用途管制和生態(tài)修復(fù)必須遵循自然規(guī)律,如果種樹的只管種樹、治水的只管治水、護田的單純護田,很容易顧此失彼,最終造成生態(tài)的系統(tǒng)性破壞。”還有完整性的問題,制度不斷建設(shè)和發(fā)展,系統(tǒng)的建設(shè)思維還不太夠,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做法還沒有改變,因此要強調(diào)“系統(tǒng)完整”。
“加快”也很重要。夏光說,現(xiàn)在看來,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建設(shè)速度、進度,均比生態(tài)文明領(lǐng)域要快,相應(yīng)的制度建設(shè)也更完善。而生態(tài)文明提出得相對較晚,法制體系不健全,強度也不夠。比如,機構(gòu)、人員經(jīng)費都還不足;相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環(huán)境壓力而言,生態(tài)文明制度建設(shè)比較滯后;《環(huán)境保護法》目前仍然是“軟法”等。要在2020年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biāo),生態(tài)文明制度建設(shè)要加快,才能跟上需要,才能更好地推進向市場和社會放權(quán)等。
關(guān)于監(jiān)管和執(zhí)法,《決定》指出,“建立和完善嚴(yán)格監(jiān)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huán)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huán)境監(jiān)管和行政執(zhí)法”。
王毅認為,我國環(huán)境監(jiān)管的體制一直不完善,而環(huán)境保護部門的主要作用就是監(jiān)管。但大部分地方?jīng)]有獨立的環(huán)境執(zhí)法,沒有相匹配的執(zhí)法隊伍,還有司法、問責(zé)等方面也存在問題,都需要一步一步開展。
“制度、體制的建立健全還事關(guān)多個利益相關(guān)方能否有效管理和參與環(huán)境治理的問題。”王毅說,環(huán)保不單是環(huán)境保護部門的事,涉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等多個要素,需要多個部門之間協(xié)調(diào)管理,而現(xiàn)在沒有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管理的機制,部門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機制也不健全。另外一個層面,區(qū)域性、流域性的管理體制缺失,涉及到省以下的基層環(huán)保部門管理機制也需要改革。就社會與市場而言,目前所有利益相關(guān)方參與仍不足。
因此,3個關(guān)鍵詞就成為今后環(huán)保工作的重點方向。夏光說,環(huán)保系統(tǒng)有些人有相當(dāng)程度的技術(shù)思維,習(xí)慣于用技術(shù)思維的辦法管理環(huán)境問題,人員也主要來源于工程技術(shù)序列,但在加快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時代,要盡快轉(zhuǎn)入制度思維。所以,“‘加快’,首先是環(huán)保領(lǐng)域要從上到下改變思維角度,把更多的精力轉(zhuǎn)移到制度建設(shè)上來,包括立法、執(zhí)法等層面。”
馬上開始行動,但不能急于求成
“需要馬上開始行動。”王毅說,核心仍是需要從法律層面建立制度,建立有效的管理、監(jiān)管體制,使已有的政策或機制能夠起到應(yīng)有的效果;長期來看,依靠行政抓環(huán)保的辦法不可取,而要靠一系列完善的制度,更好地配置社會、市場等資源;尤其是節(jié)能環(huán)保產(chǎn)業(yè)等,更不應(yīng)寄希望于短期成效。
也就是說,路徑已然明確,但實現(xiàn)過程需要一步一個腳印。王毅說。比如,目前進展較快的排污權(quán)交易,交易的環(huán)境資源不一樣,相應(yīng)的市場體系構(gòu)建難度也不一樣。
“排污權(quán)交易有幾個基本要素。”王毅認為,一是統(tǒng)計和監(jiān)測體系要很好,否則就無從談起。而目前我國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和監(jiān)測體系不健全,還有很大差距。比如碳排放數(shù)據(jù)是由統(tǒng)計得來的,而二氧化硫排放數(shù)據(jù)是監(jiān)測得來的。二是要明確污染物控制總量。總量不限制的話,就無法確定價格建立市場。三是要有交易制度的建立,比如怎么確定初始產(chǎn)權(quán)分配、交易程序?近期和遠期的一級市場、二級市場如何建立和協(xié)調(diào)?最后,要探索有效的市場化運作。比如開展多種排污權(quán)交易試點,成功之后通過試點經(jīng)驗推廣。
像空氣資源、水資源,國外有比較成功的經(jīng)驗。“但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本身就不很完善,環(huán)境保護領(lǐng)域的市場又是新興領(lǐng)域,從心態(tài)上不能急于求成。”
此外,關(guān)于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領(lǐng)域的市場,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產(chǎn)品”多樣化、多層次。王毅說,“除了有污染排放總量,還有環(huán)境品質(zhì)的問題。此外,還有環(huán)境資源的功能結(jié)構(gòu)以及其他很多不能或者難以量化的因素。這些如何貨幣化、價值化,都需要科學(xué)考量。”
《決定》已經(jīng)發(fā)出了信號,并顯示了政府的決心。“一系列要求的提出,有利于促進現(xiàn)有法律得到有效執(zhí)行,同時促進現(xiàn)有制度的施行。”王毅說,長遠來看,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取得實效,仍然要靠制度來說話,逐步推動管理、市場等方面的轉(zhuǎn)變。
王毅:環(huán)保工作需利用市場機制破解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