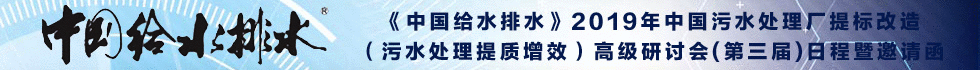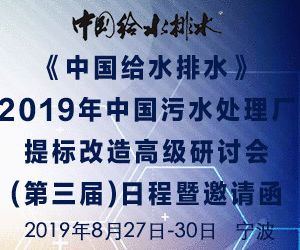最近,中央成立了經濟體制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決定由中央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環保部主要領導組成領導班子協調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研究。2014年2月初,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提出“從宏觀戰略層面切入,從再生產全過程著手,從形成山頂到海洋、天上到地下的一體化污染物統一監管模式著力,準確把握和自覺遵循生態環境特點和規律,維護生態環境的系統性、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增強環境監管的統一性和有效性”“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由于周生賢是改革領導小組的重要成員,文章因此受到有關部門和社會的格外重視。一些來源不明的改革版本在網上瘋傳,有的傳出環境保護部要兼并國家林業局,在有關會議上,雙方官員為是否合并吵得不亦樂乎;有的傳出把國土資源部的資源管理職能并入環境保護部,引起環保界和經濟界廣泛討論。這種造勢引起一些人的擔憂,甚至擔心自己的崗位和飯碗因為撤并受到影響而產生抵觸情緒。
誠然,我國霧霾天氣頻發和流域水污染整體沒有改善的現實,既說明我國的環境法律制度和機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也說明我國環境監管體制無法發揮符合實際需要的作用。從理論上分析,周生賢提出的“從形成山頂到海洋、天上到地下的一體化污染物統一監管模式著力”“增強環境監管的統一性和有效性”,符合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護整體性和相關性的環境科學理論,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環境保護部將直接管理一切環境污染、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保護的事項。周生賢在文章中提出了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六個主要任務,并未明確提出環境保護部要收納國家海洋局、水利部、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的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利用職權,相反,卻謹慎地使用“區域聯動機制”“海陸統籌”“信息互通互換”等措辭,并且提出“有序整合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監管力量,有效地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這些體制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并未涉及具體改革方案。由于周生賢曾擔任國家林業局局長,倒是文章闡述的第三個改革任務出人意料地提出“健全國有林區經營體制改革,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引起林業系統的擔憂。筆者認為,該文屬于個人的學術文章,加上作者曾有在國家林業局任職的經歷,文章有一定的自由發揮屬正常。另外,該文是關于管理體制的,不僅談了監管體制,還在改革的主要任務中大篇幅談社會管理體制和機制改革,屬于在國家治理體系之下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的文章,因此,民間不應過度解讀。
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背景下,環境監管體制的改革應針對現實問題,在環境管理體制改革的大視野下進行,堅持以下四個原則:一是科學設置和互助制衡原則,即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設立堅持既切合環境問題的自然科學屬性,也符合管理體制和方法的社會性屬性,堅持國家治理各方主體作用的互助性和相互制衡性;二是政府主導和民主參與原則,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開展民主決策、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使環境保護的國家治理公開化、透明化,鞏固治理的合法性;三是以人為本和法治治理原則,即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四是域外借鑒與本土創新原則,即堅持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于推進環境保護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在具體的改革措施方面,應從以下三個領域入手。
一是圍繞環境監管統籌性和權威性不夠開展改革。雖然《環境保護法》授予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護職權,但是環境保護部門并沒有發揮好這一角色。這并不意味著其他部門把生態保護甚至資源開發利用職權都交給環境保護部門,讓它一家孤家寡人式地“獨立”開展。環境問題發生于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具有系統性和相關性,如果讓管理經濟、社會發展的部門交出自己領域環境問題的直接監管權,讓一個屬于業務部門的環境保護部門去監管,就會出現權威性、專業性和有效性缺乏等新問題,難以具有實施可行性。只有把環境保護工作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各主要領域,建立健全各領域責任機制和職責實施機制,讓管理這些領域的部門直接分管環境保護,讓環境保護部門享有實實在在的部門和區域監督權,環境保護才有出路。現在的問題是,各部門的責任機制和職責實施機制不健全,直接監管責任虛化,環保部門無法協調其他部門。因此要發揮環境保護部門由《環境保護法》確立的統一監管作用,重點必須而且只能是創新機制,使現有的職責分工生根發芽。有必要借鑒安全生產綜合監管和專門監管的分工合作經驗,建立環境保護部門有權統一協調規劃、統一協調環境保護行動、開展監督性執法、調查所有環境損害事件等統一監督管理機制,將統一監督管理職責細化為“綜合指導、綜合協調、綜合監督和綜合服務”。在監督性執法和事故調查處理方面,國家應當借鑒安全生產綜合監管的經驗,授予環境保護部通報違法的部門和區域、約談違法的部門和區域行政首長、提出獎懲建議等監督性權力,使其他直接監管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利用的部門以及所有的行政區域都服從環境保護部門的綜合指導和協調。與此改革思路相適應的是,應當在環境保護部內組建環境事故調查司、環境保護綜合協調司、環境保護綜合監察司等履行綜合監管職責的機構。當然,國家如認為適當,也可把一些部門無法開展或已虛化的生態監管職權,如農業部門的農業生態監管職權,劃歸環境保護部;把一些專業狹窄的副部級資源和生態監管部門如國家林業局等,撤并至環境保護部。
二是圍繞政府監管權威性和有效性不夠開展改革。反思頻發的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政府首先承擔監管失察的責任。由于黨委領導政府開展工作,理論上講,黨委班子也要承擔黨紀甚至法律責任。但目前各級黨委環境保護領導責任虛化,因此受到處罰的往往是政府系統人員,很少涉及黨委口的省市縣委書記。黨委如果不重視,不建立黨委的領導責任機制,政府的環保工作就很難抓起。目前,環境保護責任重大,政府口排名靠前的副職行政領導往往不愿意分管。分管的副省市縣鄉(鎮)長排名靠后,他們提出的人、財、物等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請求難以得到本級黨委常委會和政府常務會的足夠重視,于是環境保護就被推到看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尷尬境地。中央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精神,完善制度、強化責任、加強管理、嚴格監管,把環境保護責任制落到實處。該要求強調了黨委責任,并把其排在政府責任之前,可見落實黨委領導責任之重要。此次體制改革,應當借鑒安全生產經驗,建立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和齊抓共管的責任構架,讓黨委常委會定期討論環境保護問題,讓專門的黨委常委聯系環境保護,讓所有的黨委常委在分管領域配合環境保護工作等。只有這樣,環境保護工作才有現實的權力和責任基礎。目前,環境保護的黨政同責架構在河北張家口市等地得到很好實踐。
三是圍繞國家治理體系中市場和社會角色不足開展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要求,要求公權部門、社會主體和個人在法律的框架下,通過法律授權、法律規范或者法律不禁止的渠道、方法、程序,發揮各自作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解決國家和社會問題。公益性、社會性、民主性、協作性和協調性是環境保護國家治理的基本屬性。為此,應當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管理體制改革:首先,按照《民事訴訟法》要求,修訂《環境保護法》和專項環境立法,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發揮司法機關和社會的有序監督作用,把行政權力置于由司法和社會權利編織的籠子;其次,下放和取消一些許可,通過專業中介、商會、行業協會等市場自身的治理,通過社會中介機構、社團組織、新聞媒體的社會治理和社區治理,使政府從很多角色越位的領域抽身,拿出更多精力專心于環境監管和環境建設工作;再次,制定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實體和程序性規定,使社會組織和公民有序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工作,彌補政府監管視野和監管能力的不足,預防和化解政府大包大攬產生的社會矛盾。只有這樣,實現環境保護權力和權利的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使環境保護國家治理在健康的軌道上實施。
體制改革最忌諱動輒提出毀掉一個現行體制,建立一個充滿新問題的全新體制,特別是一個部門既審批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許可,又負責生態環境的保護,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可行的辦法是,分析現行體制的不足,參考其他專業領域好的做法,深挖潛力,通過創新和完善予以解決,而不是盲目地全盤否定。只有這樣,才能既堅持制度自信,也與時俱進。
作者簡介:
常紀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中國環境環保監管體制改革”研究項目負責人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