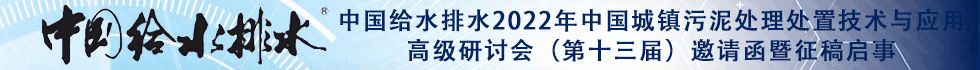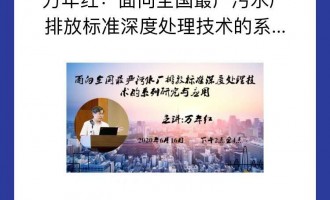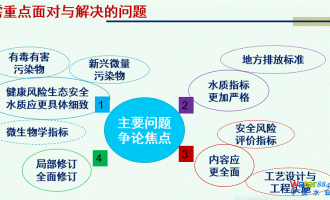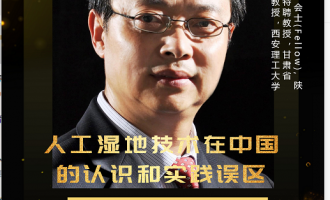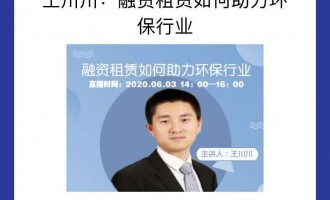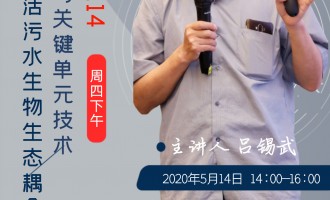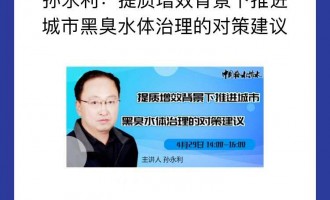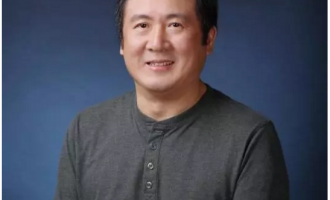很多人說應不應該建地下污水處理廠?我想我們爭論的內容不在一個起點上。我們是不是應該讓我們的孩子享受到我們兒時的快樂?這是我們爭論、討論的點。
歷史給予我們將污水處理賦予新的內涵、創新污水處理商業模式的機會,我們要抓住歷史的機遇。這要寄希望于設計院和水務公司,作為學者,我僅僅是提出一個倡導。
隨著我國污水處理廠建設要求的提高,加上土地資源緊缺的形勢,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的地下污水處理廠成為行業新的關注點。在9月11日開幕的“2015(第七屆)上海水業熱點論壇”上,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國家環境保護技術管理與評估工程技術中心主任王凱軍發表了題為《地下污水處理廠的設計理念、技術理念和運營模式》的講話,共同探討地下污水處理廠建設極致化之道。
以下為現場文字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我們的春天被城市的發展方式扼殺了
今年是卡森《寂靜的春天》發表50多年,所有的生物都被DDT殺死了,聽不到鳥的聲音,是非常寂靜的春天。但是我想問大家,誰在家里可以聽到鳥叫蟬鳴?如果可以聽到,你們在大城市當中是幸運的。誰在家里聽不到交通噪聲?我覺得你們也是幸運的。早上起來,我們想聽到的鳥鳴確實沒有了。
這個PPT當中的蜻蜓、蟋蟀,我們兒時的伙伴,現在大家的兒女已經很難看到了。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東西,這是對國內學者的統稱:海龜、土鱉。
我們的春天沒有被DDT殺死,但是被城市的發展方式扼殺了。北京在前幾年說不能有大面積的水,但是我看到一本書,說北京是“水鄉北京”。清華所在地海淀歷史上也是水鄉,是不是40、50年代和現在有大的變化?降雨量其實沒有大的變化。應該是被我們搞城市水環境的破壞了。蜻蜓少了,是城市發展的結果,城市的水環境被我們破壞了。
如果大家對這些畫面有所感觸,是否應該進一步考慮污水處理能否成為生態建設的重要環節?你愿意選擇什么樣的污水處理廠?如果這些可以引導我們膚淺的思考,我想下面我講的東西大家會接受。
不同文明的特征與污水處理的關系
我們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今天的生態文明,工業、生態文明之間還有一個信息文明。
工業文明的特點是以大城市、大建設為標志,造成了能源資源的大量消耗、生態失衡、環境污染。比爾•蓋茨有一篇報告,說中國三年的水源消耗量是美國過去100年的水源消耗量。這也代表了工業時代的極致,我們國家走在了工業時代的極致。
大規模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美國的Stickney污水處理廠是世界最大的,把污水從地下90米提升上來。新加坡的NEWater,也是工業化時代的,以技術極致化來解決。
“超越福特式的大規模、集中式處理的舊框框是工業時代的觀點,不是文明時代的觀點”。
城市污水與相關技術領域發展
從我們國家來看,十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我們貫徹的思想,到現在比較明晰的是生態文明,強調了持續發展。以前我們講可持續發展,但我認為生態繁榮高于可持續發展。
我們的行業做了什么?我們認為我們搞環境保護就是搞生態文明,其實不然。我們可能是以破壞生態的方式在搞生態文明。污水處理,我不展開了。在技術路線上,我們在有很多種可以選擇的綠色道路的時候,選擇了灰色或者選擇了非綠色。現在我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這張片子在10年前我也說過,各行業都在搞綠色化,我們這個行業在低碳、綠色化方面認識有限。"十二五"大家才做綠化。我們認為搞環境保護的,就是搞綠化的,這個觀念現在要改變了。
這個時代,我們認為污水處理是低碳、資源回收的。國外有很多探討,在垃圾處理上,美國提出了綠環。垃圾處理廠上面是公園,下面是垃圾處理設施,綠環系形成了城市景觀。
農業上現在倡導都市農業,美國科學家預言2050年垂直農場將問世。不同的行業進展非常快。污水處理方面我們提出:水質可持續、能源回收、資源循環、環境友好。
按照這樣來講,我們的污水處理廠應該承載更多的功能、更低的負荷、更美的景觀、更少的占地、更低的投資,更高的生態價值。我們應該是低碳、資源回收、零排放的生態污水處理系統。
地下污水處理廠的價值分析
這幾年我們突然發現地下污水處理廠在我國應運而生。我國有30多個地下污水處理廠,絕對數量很少,但增量達到了10%左右。直接投資達到了增量的12%,帶動的投資可能超過30%,地下污水處理廠是地上污水處理廠1.5到2倍的投資,但是其帶動的景觀投資是10倍。
它有什么好處?減少了鄰避效應。肖家河污水處理廠,在海淀寸土寸金的地方,導致周邊1000多畝地沒有開發。我們知道公園和水體可以提升土地價值,(這個水廠的建設)讓北京陶然亭和紫竹院周邊的土地價值都得到提升。如果我們地下污水處理廠可以改造成景觀公園,可以提升周邊的品質。
我們看美國的綠島,如果我們的污水處理廠以這樣的形式來建設,可能情況不一樣。以北京為例,直接占地達到3000多畝,但這只是一個假設。
現在的地下污水處理廠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有三個進步性問題,三個管理性的問題。建設投資高、通風除臭高,比傳統污水處理廠高30%到50%。技術上來講,我們有兩種反應器,一種是懸浮生長和生物膜。現在大家采用懸浮生長系統。
地下污水處理廠可以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這是荷蘭的例子,國外已經有幾十座,是完全商業化的技術。當時提出鹿特丹的一個污水處理廠,如果用顆粒污泥,很多綠色面積都可以使用。另外我們進行的微沙加重沉淀、磁分離等等,和地下污水處理廠結合的話,也有很大的潛力。
奧地利一家小的公司發明了納米絮凝劑的技術,兩滴加進去可以改善沉淀性能。和地下污水處理廠結合效果很好。所以我說,產生了需求,我們對技術才會有更高的追求。納米絮凝劑沉淀時間只有3到5分鐘,這是已經大量實現的技術。
地下污水處理廠的模式與技術發展方向
現在地下污水處理廠,大家一看都認為是沉在地下,其實有三到四種模式,一種是單層加蓋,一種是雙層加蓋,一種是半地下,第四種是地上全封閉加蓋。我們現在設計規范差了一些東西,我們和航站樓、大劇院一樣,簡單地在上面加一個罩子按到了地下。我們看了國外的航站樓,再看中國的航站樓,感覺是資源浪費的形式。地下污水處理廠實際上也在走這條路,簡單地扣在地下。
我們提出了兩種方式,一種是城內污水處理廠,一種是城郊污水處理廠,我們希望可以結合。比如社區公共文化,景觀、公園、科普、教育,可以和我們的污水處理廠建設結合在一起。在城郊的,我們可以更注重生態性、市民的參與性和設施的經濟性。我們最終從負資產變成正資產,我們做城市生態綜合體。
我們的理念提出之后,北京一個很大的污水處理廠改變了,做成研發中心,形成創意園區。和水景娛樂公司合作,要做水活力樂園、水生態體驗和水博物館,從負資產走向正資產。
總后我總結一下:我們認為地下污水處理廠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重要選擇之一,我們不說是唯一的選擇,這個有很大的空間;
通過地下污水處理廠的技術探索,可以推動與促進污水處理技術進步。你需要提出更高的需求,我們才有研發的動力;
第三,地下污水處理廠不是污水處理廠本身,是生態建設的抓手,是行業實施生態文明的一種體現,政府和社會應該積極倡導,建設以污水處理廠為核心載體的城市生態綜合體。
很多人說應不應該建地下污水處理廠?我想我們爭論的內容不在一個起點上。我們是不是應該讓我們的孩子享受到我們兒時的快樂?這是我們爭論、討論的點。
歷史給予我們將污水處理賦予新的內涵、創新污水處理商業模式的機會,我們要抓住歷史的機遇。這要寄希望于設計院和水務公司,作為學者,我僅僅是提出一個倡導。